“艺”起战疫|中文系学生如何解读《催眠师甄妮》
冉冉的《催眠师甄妮》(重庆出版社出版2022年9月出版),多少可以抵抗孤独、缓解焦虑、走出失眠困境,因为这部小说可谓是献给都市失眠者的一味良药,为现代迷失人生提供了精神导引。近日,西南大学李永东教授组织中文系学生阅读、讨论了这部小说。讨论围绕三个方面展开:“引文”的作用;人物身份与空间结构;催眠题材对生命理想的表现。以下是2020级中文系博雅班部分学生的讨论发言,分享给大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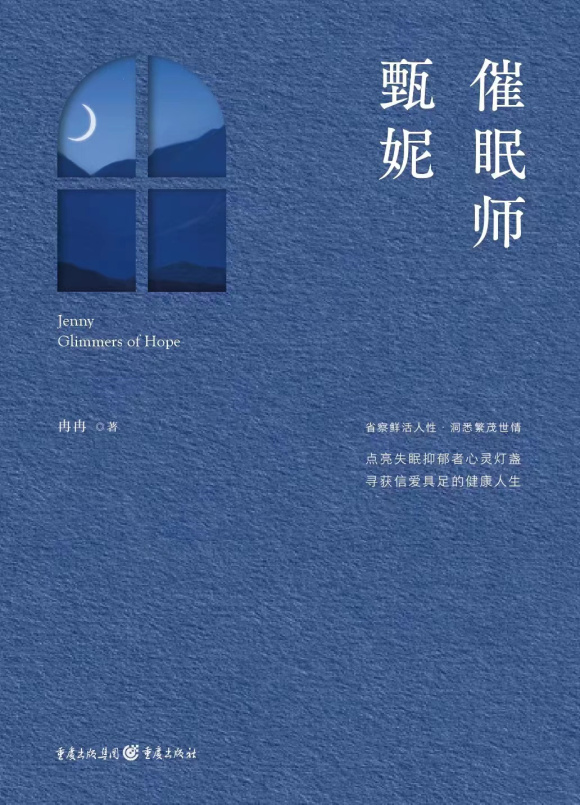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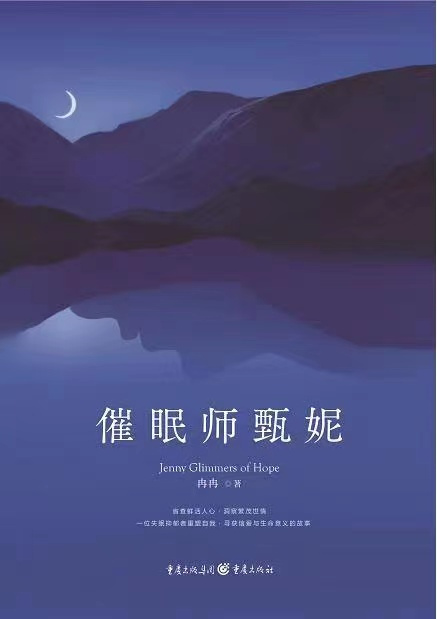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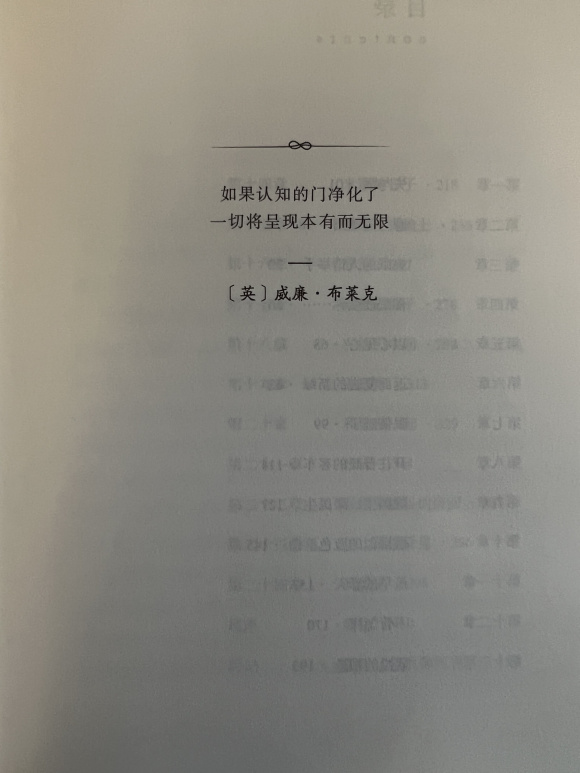
邢佳琦:
观察和联想后不难发现,引文和封面或许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封面的设计可以看作是一扇带有窗户的门,只能通过窗户看到一弯山月,对应“认知的门”。湖、山、月交相辉映,融为一体,展现出的是自然之夜,是催眠之静,是睡眠的和谐安详,是精神之纯净悠远旷达。若将内封图旋转,则可见山在湖中的影子呈现出一位女子侧颜的轮廓,这位女子或许就是甄妮,山对湖的凝视就是甄妮对于自己内心的凝视与探寻,是对于事物的本真与纯真无暇精神的凝望沉思,是无数个死去的故我与一个个不断苏醒的新我的更迭洗涤,是蒸馏过后崭新的生命与人生。在甄妮一次次“死后重生”的过程中,她不断地走向、靠近真实的自我,发现生活的本真。
“如果认知的门净化了,一切将呈现本有而无限”,即认知若回归于原始状态,则宇宙便也会回归原初,不再被约束,由此照应了小说中有关于“催眠”“生死”“爱恨”等主题。作为引文,它以短短一句话总结了作者的写作观乃至人生观、价值观,并尽可能地将读者引向了更辽远广阔之境,打开了小说阅读的可能性。
曾梓莘:
美国自然催眠法的先驱艾瑞克森指出,“在催眠状态,患者能打破自己结构化的思考模式,同时尝试自己心理结构的另一种工作方式。”小说中的引文可以看作人物的“代言”。引文的出现使得整篇小说成为一个由多种声音与意识交织起来的文本。但比起让文本呈现出完全混乱的状态,引文恰恰符合语境且具有理智的色彩。“引言”是否可以看作无法言说的潜意识的理智化的表达?我们透过这些引文窥探到了一个隐藏于其中的潜意识,我们试图透过引文看到潜意识的过程,其实就类似于催眠师进行催眠的过程,使得小说变成了可以互动的对话。
从催眠角度来看,甄妮的身份经历了“不接受治愈——转移治愈——治愈他人——自我治愈”四个阶段。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认为人面临挫折会产生多种防御机制,其中前两个阶段就类似于“压抑”与“转移”。在这两个阶段,我认为甄妮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接受自我,没有真正面对自己的精神问题并展开疗愈。她先是拒绝,然后通过对别人的催眠来转移自己的需求与痛苦,可以看到的是她过于相信自己伪装的“外壳”,没有与问题和解,最终造成了精神的崩溃以至于再度远走他乡。而在普旺县生活的这一阶段,她事实上与自己面临的诸多问题彻底隔绝开了。她实现了一个短暂的与“从前的自己”分离的状态,在这里她是“栗医生”,不再是甄妮。也是这样一段时间,她重新建立了理智,并以一个坚强的“意识体”的身份在外界的引导下试图对过去的一切进行反思与治疗。可以看到,从此之后,甄妮的戾气与焦虑减少了,心态更加平和,包容别人也包容自己。在米耶的那段时间里,真正从帮助他人中实现了对自身心灵的洗涤。最终,她在自我和解的过程中结束了生命,完成了主动的和解。
催眠原理利用了人类思考的两个不同层面:意识和潜意识,催眠就是越过意识直接和潜意识对话。失眠即无法入睡,无法让我们的意识(自我的、超我的)放松而进入到潜意识(本我的)层面。催眠与之相反,正是要回归到潜意识的领域里去。但我们始终不能忽略,催眠的过程中仍有一个完全由意识控制的“催眠师”的存在。访问潜意识,其实是通过确立“什么是真正的自我”来抵达生命理想。我认为“潜意识”就是真正的自我,事实上主角的经历正是她的潜意识不断受到干预的过程。小说在一个很巧妙的地方结尾,即甄妮遭遇车祸,结尾的叙述近乎一种意识流的状态,这是甄妮的潜意识,但作者并没有让甄妮在昏迷中死去,而是让周围的人不停地试图与她沟通,甚至有一种类似于“玄学”的氛围。“她让自己放任地观察自己的观察”这句话,在我看来是意识积极与潜意识对话,并最终达成和解的过程,甄妮此时既是催眠师,也是被催眠者。我觉得这是在表达,无论是“完全被本能驱使的人”还是“完全由理智控制的人”都不能算是完整的人,甄妮在生命的尽头达成了意识与潜意识的和解,完成了本我的声音与外部声音的和解,坦然地接受过去的一切经历,面对真实的困境经历,最终选择以谅解、善良的心态终结一生。精彩的生命可以经历一切不堪,而高贵的灵魂就是暴露自我后的平静与接纳。最终在实现自我和解的基础上完成对外界的正向输出,用谅解与善意构建起内外沟通的桥梁,使得自己与他人都抵达平和。
姜蓓蒂:
小说的“引文”常常被理解为是作者借圣贤言论及故事来丰富自我表达的一种有效手段,适当的“引文”是对人物故事叙述的补充说明、预示影射。如在主题表达上,小说多次引用“舍身喂鹰”的故事,目的不单在于对甄妮一行志同道合之人的虔诚“自救”与“救他”行动的溯源探讨,更是借先贤故事说明身心遭遇的创伤本就是“渡己”“渡人”的必然过程,而苦难的消融的背后则是崇高精神之塔的高矗。在结构功能方面,“引文”更像是暂时的故事叙事消减,在其蕴含的精神梳理中集聚生命重新迸发的蓬勃之力,螺旋上升,层层深入。就人物关系上看,不断地对先哲言论、故事的引用,实际上有效缩短了甄妮同先哲的时空距离,同时也一定程度地割裂了人物间的事实亲疏关系。
小说中的失眠、催眠似乎是人本身高贵灵魂迷失和迷失灵魂重归的隐喻。小说人物的失眠原因,往往都是人们常常会面临的诸多个人社会问题,囊括了亲情、友情、爱情,婚姻和事业的交错,早年磨难和半生救赎等,但总的来看无非是人活于世的七情六欲带来的人生八苦,这些痛苦磨难也成为了人们原本自由高尚灵魂的永恒羁绊。这羁绊就像缠绕溺水人的藤草,掩盖着人们的本心本性。而催眠则是对身处羁绊无法自拔的人的一次灵魂洗礼,给了人们一次重新相信自己的勇气,即所谓的战胜困难之前要有面对困难的勇气和战胜困难的决心。催眠在这时也可视为“催醒”,就如陆王心学以为的“吾心即是宇宙”“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一般,让自己面对世界苦难能够保持超然的清醒,淡然处之,而非生物本能的趋利避害。
吴欣然:
我认为小说的所有要素都是为主旨服务的,《催眠师甄妮》也是如此。在主题表达方面,小说讲述的尸毗王割肉救鸽、“贫民圣人”特蕾莎等引文表现了人性的圣洁与仁慈,更是对整部小说正大从容的美学风格的映射。另一方面,引文中的先哲故事正是甄妮、新月婆婆等人物品格和人生走向的代言,尸毗王“舍身喂鹰”是为了拯救无辜的鸽子让自己承受痛苦,但这种痛苦背后是自我价值的升华。甄妮和新月婆婆都是从最刻骨铭心的伤痛中涅槃重生,造就了高尚慈悲的品德,这种引文和主人公的相互照应正是结构中串联的巧思。小说还有一处,舒那茜引用了泰戈尔“尘土受到损毁,它却用花朵来报答”一句来用作挽联。舒那茜虽然几度伤害了甄妮,但也无比了解她,以读心人的身份将甄妮的心境和小说的主旨向读者娓娓道来,人物之间的关系也由单维走向更复杂的境地,我觉得这也是另一种对人性的探索和反映。
邓宇婷:
引文中的“认知之门”指通向内心真实自己的阻碍,“净化”指向内心升华和自我突破,“无限”是指超越现实痛苦后心灵获得解放的状态,与之相对应的“有限”即前半句中的“认知之门”。引文起到了阐释符码的作用,小说围绕“认知之门”如何被“净化”及被净化之后的“无限”的样子来展开。以“净化”为切入点,小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失去挚友回到壹江的甄妮开始从事催眠师的情况,并且采用插叙的方式向我们展示甄妮不幸的过往:父母离异、失恋、奶奶失踪、挚友去世等,这一阶段甄妮虽然受到催眠工作的影响,开始理解、包容、关爱他人,让一点点阳光照入心中封闭的小黑屋子,但是还没有完全消化过去的不幸,而且最后诊所的医患纠纷将她打回原形,又一次陷入无尽的痛苦,这一部分基本上属于铺垫。第二部分是甄妮来到普旺和米耶,受到裴医生和新月婆婆的感染,学会爱与奉献,写了甄妮被“净化”的过程。第三部分是甄妮回到壹江办微利医院和为救好友新绿而受伤之事,表现“净化”之后的高贵灵魂。引文作为阐释符码暗示了主题,也设定了小说的结构。
回诺亚:
《催眠师甄妮》主要的空间背景有壹江、普旺和米耶。甄妮在三地之间转换的时候,有着不同的反应。甄妮在小说中有两次近乎于“逃跑”的行为,一次在初返壹江听说了奶奶的事之后从车上逃离,一次是在登雅的追思会上剥去衣服后逃离。这两次逃离也对应着甄妮的蜕变,第一次逃离时甄妮尚采取着逃避的姿态,而第二次逃离伴随的脱衣服的动作,象征着甄妮对于自我的表白与解剖。但是在去往米耶时,甄妮已经不再采取“逃跑”的行为,而是坐皮卡去到米耶的,表明在普旺的修行让甄妮的灵魂更加成熟与坚强,最后甄妮受到新月婆婆“米耶即壹江,壹江即米耶”的启示而返回壹江,这时的甄妮在进行空间的转换时已经完全出于自己的选择了,这种在三地之间流转而最终主动选择返回原地的行为体现着甄妮灵魂修炼的完成。
高贵灵魂的塑造其实是一种自我疗愈与自我塑造,催眠师看似是一个服务与救治他人的职业,但实际上甄妮的第一位患者就是她自己,并且她也多次提到,她的催眠只在于引导,而真正使患者治愈的是患者自己。小说中常常提到壹江的失眠患者之多,这也在说明人们常常有痛苦和灾难,通过催眠来解决失眠,传达出通过自我修行疗愈自己灵魂的希望。同时,高贵灵魂也具有向外映射的能力,能够影响他人,甄妮对他人的催眠、裴医生和新月婆婆对甄妮和众人的影响,都是这种高贵灵魂的体现。
陈心悦:
《催眠师甄妮》的背景是世纪之交的城市化进程,地跨城乡。小说的空间结构从壹江到普旺、米耶再到壹江,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转换,在空间变化中暗含了甄妮在跌宕的经历中进行的精神灵魂的历练与升华。而这些自我重塑跟所处地域脱不开关系。与裴医生和新月婆婆的相遇,普旺米耶的小环境,潜移默化改变了甄妮的视野和看世界的方式,让她接触到一些此前生活圈里没有的人。再回到城市,甄妮的情感状态由一败涂地转而尝试自救并且救助他人,开起“离离工作室”。来到工作室的,有“都市病”患者(登雅、老貂、廖老师等),也有回乡启蒙扶贫治愚的乡建乡绅后代(裴医生、新月婆婆)等,其命运沉浮也无不跟时代与地域环境相关连。我认为,城市的空间迁移,是实际空间的迁移,也可以是情感的迁移。可以理解为来到城市产生的情感变化(如:都市病);也可以理解为“自救”之后,从城市再返回乡村,如裴医生、新月婆婆那样回乡启蒙治愚的迁移。因而,小说的空间结构,除了甄妮的空间迁移,也体现在人物的情感生活和命运沉浮中,这其中恰好反应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嬗变、城乡人心的浮躁动荡。
王思宇:
小说空间结构的转变伴随着人物心理状态的转变。这一过程,像是一个“汲取养分-养分反哺”的循环过程,更是人物理想的塑造过程。
空间的转变模式为“城市-乡村-城市”,主人公甄妮的心理也由最初的暗淡、绝望、悲恸、封闭的状态,到通过乡村的所见所闻和参与乡建慢慢自我疗愈、自我成长,再到回到城市后有重新开始的勇气与决心,并充满了原谅过去后的释怀、平静,转变为试图传递正义、善与爱的向善向美的状态,人物的心理状态随着地理空间的变化也在成长变化。
这其中的转折点是普旺、米耶的乡村生活。甄妮也正是在这段时期汲取了大量的“养分”,并自我医治。这次的乡村之行,教会了甄妮应该选择什么,教会了甄妮如何将自己的目光投射出去,回归本心。或许人们在审视自我的时候很难割裂地发现意义,但如果将自我放在时间或社会的洪流中,虽然渺小微茫,但也有回响。
再回到城市的时期,便是甄妮“养分反哺”的时期。被真诚的善与爱照亮的人,也会将光收集起来,照亮他人。“远离天堂——为地球上/陷入黑暗的人 点燃他们的灯”甄妮自己经历过黑暗,也曾被别人救赎过,体会过黑暗中见过光的样子,这份珍贵经历足以改变她的人生轨迹。或许她便是怀着这样的“感恩”之心想要将希望继续传递下去,因而继续开办了诊所,继续用“催眠”帮助更多人驱散他们心中的阴霾,让他们重获爱与健康人生。
失眠不仅仅是一种被抑郁摧压的具体化问题,也可适度抽象化。当在现实中举步维艰而感到迷茫、困惑时,往往面临两条路:要么“失眠”,要么“催眠”;要么反抗,要么和解。个人认为这大概是经历生命、面对生活的两种路径。甄妮曾经经历痛苦黑暗,这种打击与折磨使她产生出病态的心理。那时候的她在自我挣扎拉扯,似乎在反击与自我和解中反复徘徊游移,但慢慢发现自己的力量有限,无法与自己和解,更不用说反击。在去乡村的过程中便是自我和解的过程,加之在其中看到乡村中的人们面对命运无常时的反抗或沉默,她慢慢解开心结。在承认了痛苦带来的选择路径的必然性,看到了许多人各自的选择后,她不再逃避,而是选择面对,尝试自己和解,试图解开心结。现实中,多少人难以改变生活的种种,唯有说服自己,坚韧地活。
汪舒冰:
这本小说名为《催眠师甄妮》,它以失眠、催眠切入,本身就带有强烈的精神性,作者在小说中早早抛出了问题:失眠是什么?催眠是什么?可以说在一开始,小说就在施予读者心理暗示,暗示许多事物都是精神性的,也提到了精神对于物质、身体的驾驭性质。譬如,小说前半部分写到催眠解决了很多人的问题,包括疾病、焦虑、睡眠、怀孕等,这里的催眠效果主要是通过催眠师的施为来展示的。
与此同时,小说强调了人的自我价值,正如甄妮所说:“催眠其实是自我催眠”,人本身就有强大的自愈能力。如果说前面是在展示甄妮催眠术的神乎其技,那么后面的文本就是将视点转移到个体,体现个体的自主自觉性,以及身体机能与物质世界的反驾驭性。
综上,整个文本仿佛在展现一场物性与精神性的角逐,一开始提到“奇异的痒”,是精神外化为物质身体上的感受;中间甄妮先学催眠再识记人体的经历,是在感知人心与精神赖以成立的物质支撑;而后面甄妮不治身亡,则是(个体)精神与物质的消弭。
郝育蝶:
“催眠”是一个看起来带有一些“神秘”性质和陌生化色彩的活动,而“高贵灵魂”抑或是“生命理想”这样的概念内涵也比较抽象。太过于贴近人们可感知、可确定的东西反而不容易将一种精神力量表达出来,“催眠”与读者恰好的距离感,反而能让其中的内涵得到更好地表达。同时这篇小说也是在探索精神与现实、身体与意识的关系,“催眠”通过使身体和精神双重放松来达到抚慰人内心深处郁结的作用,是能够将身体与精神相连接,但是又更强调了精神的存在。在催眠这一活动中,催眠师和被催眠者也形成了一种“启发”“教化”和“被启发”“被教化”的关系,隐喻性地表达了“高贵灵魂”在“世界”中一种向周围人辐射影响的作用所在。
廖雨荷:
小说通过塑造每一位主人公的沉浮身世,或直接书写,或间接透露,写出了每一个人背后的苦难,有一种众生皆苦的意味。而其中重要的方式便是催眠。小说中表达的催眠是一种心灵净化的方式,是对潜意识的逼问与原谅。高贵灵魂指向“心”的修成正果,而催眠指向对“心”的求索,可以说催眠是一把打开心门与潜意识的钥匙,小说借此勾连产生联系,表达了对心灵救赎的思考。
韩歌卓玛:
小说选择失眠、催眠的题材来表现生命理想是一个很新颖的尝试。或许作者选择用失眠、催眠的题材来表现生命理想是因为梦境的独特性。“梦”往往是愿望的满足,“是大脑将白天的事件、童年的事件、躯体刺激等综合建模,用于满足无意识中的欲望”。而且“梦”和潜意识类似,是每个人对外界最后的防线,只要还有“梦”的存在,至少在12个小时的黑夜中,人可以无往而不至,可以天马行空、任性驰骋。但是在现代社会,失眠是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所涉及的人群极广,它剥夺了现代人“做梦”的权利,使人处在24小时的清醒状态。那么催眠其实就是帮助失眠的人找回“做梦”的能力,让患者回归生命自性,重新感受生命的快乐,那么这或许就是最大的救赎,也即“高贵灵魂”。










 亲爱的用户,“重庆”客户端现已正式改版升级为“新重庆”客户端。为不影响后续使用,请扫描上方二维码,及时下载新版本。更优质的内容,更便捷的体验,我们在“新重庆”等你!
亲爱的用户,“重庆”客户端现已正式改版升级为“新重庆”客户端。为不影响后续使用,请扫描上方二维码,及时下载新版本。更优质的内容,更便捷的体验,我们在“新重庆”等你!






















 数字报
数字报
 手机报
手机报 通讯员投稿
通讯员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