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渝文苑|从龙飞凤舞到明清文艺——师生对话《美的历程》
文/董小玉、马曼琳
“这样的著作能有多少呢?凤毛麟角吧。”这是易中天对李泽厚先生“美的历程”的惊叹。《美的历程》从历史的视角完成了中国自远古图腾到明清工艺的美学巡礼,并对各个阶段的美都进行了概念化的阐释,凸显了中国文明的别致美。为深入理解李泽厚先生笔下的“中国美学”,西南大学师生展开了对话。

美: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研究生马曼琳:美是一个极为抽象的概念。对美的理解,美学大家各有说法: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对美的强调是,要在个别事物上见出“概念”或理想;朱光潜先生借用一棵古松告诉我们,对美的感受就是一种心理愉悦的状态,是可以脱离于实用和科学之外的;而在李泽厚先生看来,美则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如何看待这种观点呢?
博士生导师董小玉:“美,是有意味的形式”的观点是由英国艺术理论家克莱夫·贝尔在《艺术》中提出的。它否定再现,强调纯形式(如线条)的审美性质,这给后期印象派绘画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这个理论认为是否是“有意味的形式”取决于能否引起非一般感受的“审美感情”,而“审美感情”又来源于“有意味的形式”,由此陷入循环论证中难以自拔。实际上,当李泽厚先生重提这个观点时,已经对其进行了修正,即用审美积淀论来进行阐释。他认为,那些似乎是纯形式的线条、图案,实际上是从写实的形象演化而来的,其内容早已积淀在形式中,因此才不同于一般的形式、线条,而成为“有意味的形式”。以青铜饕餮的狞厉美、魏晋风度的深沉美为例。
从炎黄时代直至殷周,大规模的屠杀与压迫是社会的基本动向,炫耀暴力和武功是这一历史时期的光辉和骄傲。而饕餮原为具体的动物形象,是为统治的利益和需要“真实地想象”出来的,它们以超世间的神秘威吓的动物形象,表示对统治阶级的肯定和幻想,因此,饕餮纹样往往是神秘、恐怖、威吓的象征。令人畏怖和恐惧的饕餮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准符号,是掠夺、剥削和奴役等社会内容在青铜形式中沉淀出的“狞厉之美”。
在魏晋时期,庄园经济日益巩固,门阀士族地主阶级得势,人的观念和活动从在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解脱出来,具体反映在美学上的基本特征就是人的觉醒。无论是文学中对人的生命和意义的探索,还是在哲学领域对人的内在虚无本体的探讨,皆是这一时期“人的解放”的特定社会内容在“文”的形式中溶化而成的“深沉之美”。因此,无论是哪一时期的美,都是在社会中生成的独特的“有意味的形式”。
审美风格:空漠感的人生况味
研究生马曼琳:苏轼在词中写道“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李泽厚先生在谈到以苏轼为代表的北宋诗人和以蒲松龄、孔尚任等为代表的清代文学家时,对他们作品的审美风格都使用了“人生空漠感”“人生空幻感”等相似的表述,如何理解这种跨时代的“共鸣”?
博士生导师董小玉:苏轼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人们喜爱的对象之一。李泽厚先生认为,苏轼在美学史中的典型意义在于,他将中晚唐时期士大夫们进取与退隐的双重矛盾的心理发展到了一个新的质变点。一方面,他忠君爱国,满怀抱负,谨守儒家思想;另一方面,他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一根本问题产生怀疑、厌倦并乞求解脱与舍弃,这就把中晚唐时期士大夫们追求对政治的退避上升到新的境界——对社会的退避。因此,无论是“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还是“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实际上都是与人生空漠、无所寄托之感联系在一起的。
清朝建立,儒学成为指导思想,复古主义兴起,文学则从明末清初的浪漫主义走向了感伤主义,孔尚任的《桃花扇》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这一变易的重要杰作,深层情感都是对山河破碎、家破人亡的悲痛和人生的茫然,由此产生了“人生空幻感”。与苏轼侧重个体精神表现的感慨不同,蒲松龄和孔尚松的感叹更加具体,其主题包括民族的失败、家国的毁灭,这种巨大而实在的社会内容也使得他们的空幻感有了更深刻的价值和更沉重的意义。所以,他们之间的“共鸣”是形似而非神似,在底层,仍是不同时代背景中的不同人生感悟。
哲学家冯友兰曾说:“《美的历程》是一部大书,是一部中国美学和美术史,一部中国文学史,一部中国哲学史,一部中国文化史。”通过这部著作,李泽厚先生带领我们进行了一次对中国美学、文学、哲学的“匆匆巡礼”,虽是鸟瞰式的观花,但所获得的印象绝不模糊。中国美的韵味将存留一代代人的心间。










 亲爱的用户,“重庆”客户端现已正式改版升级为“新重庆”客户端。为不影响后续使用,请扫描上方二维码,及时下载新版本。更优质的内容,更便捷的体验,我们在“新重庆”等你!
亲爱的用户,“重庆”客户端现已正式改版升级为“新重庆”客户端。为不影响后续使用,请扫描上方二维码,及时下载新版本。更优质的内容,更便捷的体验,我们在“新重庆”等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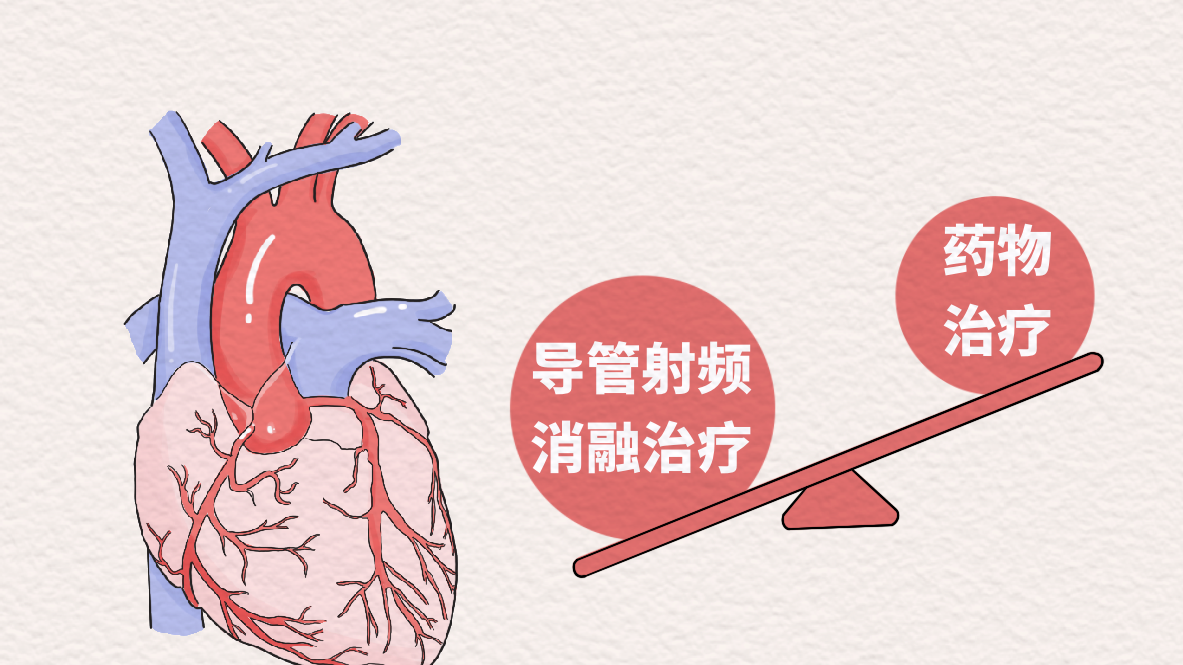

 数字报
数字报
 手机报
手机报 通讯员投稿
通讯员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