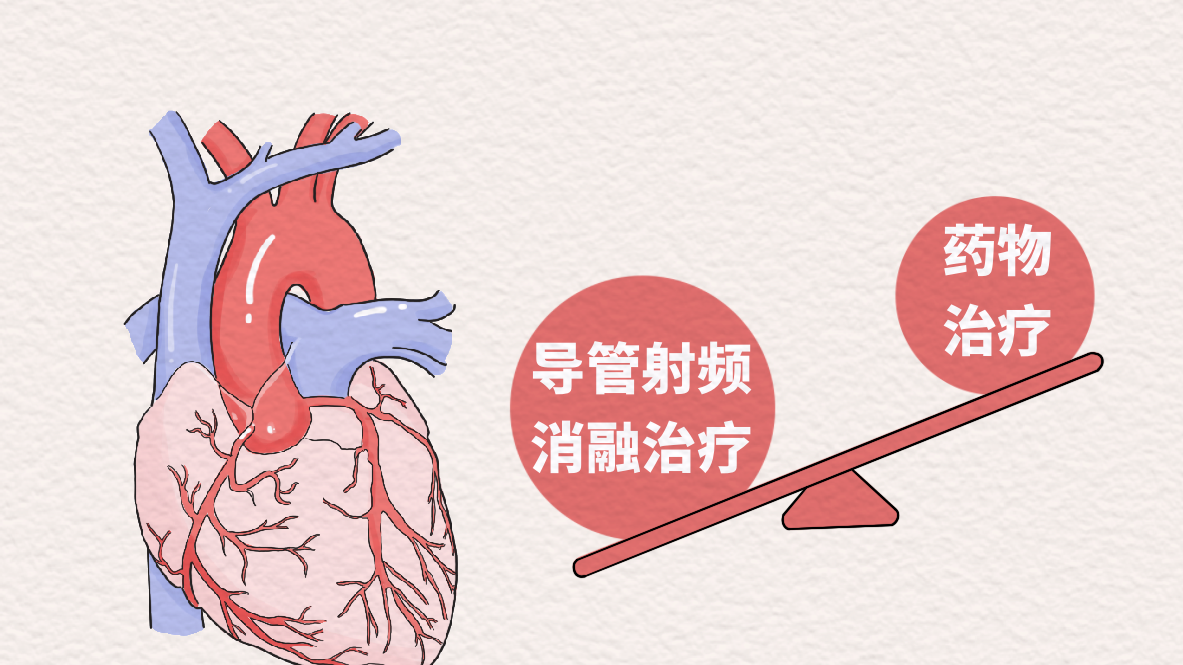平台知识产权纠纷应诚信诉讼
必须承认,我国互联网平台企业在二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为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跨界融通发展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拓展消费市场尤其是增加就业等国家战略的推动与实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近年来,各大平台企业间针对知识产权纠纷所频繁互启的诉讼数量同样不容小觑,平台知识产权纠纷应诚信诉讼。
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管辖权制度将“两便原则”贯彻始终:既要方便当事人便捷地进入诉讼渠道,又要便于人民法院高效地开展案件审理与裁判。其中,就民事侵权诉讼而言,以被告住所地或侵权行为地确定管辖法院的地域管辖原则便是现行管辖制度落实“两便原则”的直接体现。
但实践中,部分平台为谋取不正当诉讼优势,开始寻求对“两便原则”的突破,恶意制造本不存在的管辖连接点。此类行为的典型样态包括虚列与案件无实际关联的被告、为系列案件起诉专门设立公司、以伪造证据等手段制造虚假的合同签订地或者履行地等管辖连接点、通过虚高的诉讼标的额突破级别管辖限制,等等。该种行为从表面上看似是对管辖法院的合法拣选,其实质却是对管辖权制度立法原意及其本来功能的变相扭曲,源于其主要目的在于增加被告讼累、妨碍其诉讼权利的行使,而非实现诉讼便利以及促进诉讼争议的有效解决。
针对知识产权民事诉讼中原告一方人为制造管辖连接点、试图任意拣选管辖法院的行为,我国司法实践目前的主流观点是持审慎态度,这在最高人民法院当前审结的部分知识产权代表案件当中已有鲜明的展现。
例如,在2017年审结的“广东马内尔服饰有限公司、周乐伦与新百伦贸易(中国)有限公司、南京东方商城有限责任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管辖异议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侵犯知识产权案件和不正当竞争案件不能以网购收货地作为侵权行为地确定管辖。该案对合同案件与侵犯知识产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件的不同争议属性予以释明,认为在侵犯知识产权和不正当竞争案件中,当事人通过网络购物方式取得被诉侵权产品,虽然形式上与“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买卖合同”并无区别,但其所提出的侵权主张并非仅针对这一特定的产品,而是包含了特定权利的所有产品;其主张也并非仅针对合同的另一方主体,而可能是与此产品相关的、根据法律规定可能构成侵权的其他各方主体。考虑到上述区别,最高人民法院最终要求重新确定管辖法院。
裁决结果充分体现了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对“以被告住所地或侵权行为地确定管辖法院”这一通行地域管辖原则的肯定与坚守,对于后续有效规制平台企业恶意制造管辖连接点的行为而言不无启示意义。
我国民事诉讼法自2012年修订时已明确,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而在行政诉讼领域可咨参照的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保护和规范当事人依法行使行政诉权的若干意见》第十五条中,“滥用诉权、恶意诉讼等行为”早已明确成为各级人民法院的重点打击对象,因其挤占司法资源之余,还会影响公民、法人和非法人组织诉权的正常行使,损害司法权威,阻碍法治进步。结合来看,在知识产权民事诉讼领域,平台企业恶意制造管辖连接点以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显然违背了民事诉讼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属于“滥用诉权、恶意诉讼”的行为,应当得到制止并予以严厉打击。
那么,针对互联网平台企业在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中恶意制造管辖连接点的非诚信诉讼行为,应当采取何种手段予以有效规制?在笔者看来,短期而言,对于明显不适宜交由争议双方业务实际经营地之外的第三地人民法院审理的知识产权诉讼案件,各级人民法院应当通过个案裁判澄清管辖的基本原则与相应规则,并视情将案件移送回被诉平台企业所在地的专门法院(如四大知识产权法院和三大互联网法院)进行审理,以便最大限度地维护涉网络平台案件的集中审理秩序,确保涉网络平台的同类案件在审判过程中实现法律适用的统一。
实践当中,最高人民法院2020年发布的《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的第十三条中,“强化知识产权管辖纠纷的规则指引,规制人为制造管辖连接点、滥用管辖权异议等恶意拖延诉讼的行为”已被明确列为新时期我国人民法院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长期来看,从权威层面统一制定涉网络平台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管辖权争议的审理规则指引,由此更加准确地释明此类案件管辖权确定的基本原则与相应规则,以确保在网络空间知识产权治理的事业当中法律适用的统一与严整,进而推动我国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在更加规范、健康、有序的轨道上跃进。相信在我国最高司法机关的清晰认知与持续推动下,有关规则的最终出台指日可待。
(易继明)


 无障碍
无障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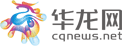
 亲爱的用户,“重庆”客户端现已正式改版升级为“新重庆”客户端。为不影响后续使用,请扫描上方二维码,及时下载新版本。更优质的内容,更便捷的体验,我们在“新重庆”等你!
亲爱的用户,“重庆”客户端现已正式改版升级为“新重庆”客户端。为不影响后续使用,请扫描上方二维码,及时下载新版本。更优质的内容,更便捷的体验,我们在“新重庆”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