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娜拉”的心灵迷失与找寻——评电影《草木人间》
文/董小玉 卢松岩
2024年3月10日,第17届亚洲电影大奖在香港落下帷幕,中国大陆演员蒋勤勤凭借《草木人间》中吴苔花一角荣获最佳女主角,为这部即将在清明档期上映的电影又增添了一份热度。该片讲述了刚毕业的大学生何目莲在发现母亲吴苔花深陷传销泥潭时舍身救母的故事,影片凭借反传销题材切入社会痛点,未播先热。该片此前入围了第36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导演顾晓刚也凭借此片荣获“黑泽明”大奖,成为该奖项历史上最年轻获奖者。此外,除了当红小生吴磊的加盟,陈建斌与蒋勤勤这对实力派夫妻档的齐上阵,也为电影赚足了关注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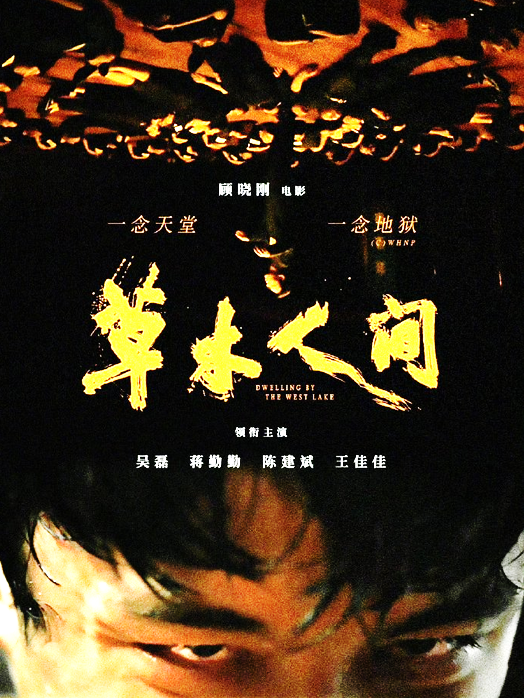
然而,电影在上映之后的口碑却两极分化。一些批评者称电影拍摄风格不够统一,剧情逻辑不够通顺,造成了观感上的矛盾和割裂,尤其是吴苔花性格的巨变尤其让观众不解。但在笔者看来,电影正是借助吴苔花这段极度撕裂的人生经历,深刻地探讨了当代版“娜拉出走”的问题。
“娜拉出走”源于易卜生于1879年发表的剧作《玩偶之家》。娜拉起初认为自己生活得很幸福,但她逐渐认清自己只是丈夫海尔茂的“玩偶”后,便毅然选择离家。出走的娜拉是19世纪西方女性争取个人主体性的时代强音。《玩偶之家》的影响并不止步于西方,1923年鲁迅发表了《娜拉走后怎样》的著名演说,进一步肯定“娜拉出走”的解放意义。但面对混乱的社会局势,鲁迅不无悲观地指出“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一思想也贯彻到了鲁迅的小说《伤逝》中,子君为爱离家出走,但又因现实的困顿而被迫归家。这揭示出了那一时期女性的悲剧,她们虽然在启蒙思潮的影响下觉醒了自我意识,但又受制于现实社会的落后,缺乏立足于社会的机会。因此,娜拉的悲剧在鲁迅的时代是命中注定的。
相比之下,《草木人间》是对“娜拉出走”问题的当代诠释,片中吴苔花陷入无限的欲望深渊,贪嗔痴俱全。她所面临的“娜拉困境”更多在于情感上的孤立无援。在影片中,吴苔花在生下儿子何目莲之后便被丈夫抛弃,只身带着儿子从四川到杭州打拼,然而,她含辛茹苦养大的儿子内心深处却始终为离家的父亲留着一个不容取代的位置,寻找生父成为何目莲决心留在杭州的最大动机,而这也阻碍了吴苔花寻找另一桩婚姻的可能。更遗憾的是,与吴苔花保持情人关系的老钱是个胆小懦弱的男人,当吴苔花遭受老钱母亲的当众羞辱时,他毫无作为。二人情人关系的暴露所造成的道德压力,直接导致了吴苔花无法继续再立足于原本的打工团体。吴苔花先后被丈夫和情人抛弃,唯一的年少的儿子不仅无法给予她足够的安全感,而且在感情上也无法与她平等相待。这种情感上的无所附着是吴苔花这位当代“娜拉”所面临的精神困境。
从这一视角来看,吴苔花随后误入传销组织的这一“歧途”,恰恰成为吴苔花寻找真我、重获精神价值路上的一种“奇途”。在电影前期,身为采茶妹的吴苔花,通过自己的努力独自将儿子抚养长大,此时她的价值感在于对物质的获取。当儿子大学毕业后,吴苔花给儿子攒下了丰厚的买房钱,这意味着她物质生活的相对富足,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则成为此时吴苔花获取自我价值的方式,这也是为何她选择在此时与儿子商讨再嫁问题的原因。但这一设想在她与情人关系曝光之后,被彻底打破。不仅如此,她还被采茶姐妹的工作团所抛弃,丧失了多年积累的姐妹情谊。此时,彷徨无助的吴苔花成为了精神的流浪儿,传销组织便趁虚而入。
当儿子以报警的方式举报吴苔花所在的传销组织时,她在雨中以愤怒的咆哮予以儿子痛击,吴苔花歇斯底里的呐喊:“我花钱买高兴行不行?我活了半辈子,我终于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这正是其自身精神危机的体现——虚妄的自我、虚妄的自尊与现实苦楚的撕裂,“娜拉出逃”与自我价值的追寻,是矛盾、更是一种与自我的对抗。她在雨中痛斥前夫的不负责任、情人的软弱无能、儿子的自私自利,影片在此迎来叙事的高潮。被雨水打湿了精致妆容的吴苔花,在雨中肆意宣泄,让儿子何目莲第一次知晓了母亲多年来被生活压抑的自我。此时的吴苔花与当初采茶女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更多呈现出自我价值迷失后的癫狂,何目莲的出场,成为拯救母亲的唯一稻草,而这也是本片的另一个亮点,即代际间的双向救赎。
这种代际救赎不仅表现在何目莲对母亲的拯救,还表现在他对母亲吴苔花精神价值的打捞。在何目莲成功搜集到传销组织的犯罪证据并将其一网打尽之后,吴苔花就彻底陷入到了精神崩溃之中,于是何目莲背起母亲向故乡的大山中走去,试图以自然之力唤醒母亲沉睡的觉知。在神秘的大山深处,何目莲失足跌入了空谷深渊,继而陷入到了昏睡之中,此时一只猛虎的出现直接唤醒了沉睡的吴苔花,对儿子的保护将这位精神崩溃的母亲拉回现实,并以动物性的本能吼叫喝退猛虎。在这段魔幻现实的叙事中,母子之间的代际关系在经历了误解、对立之后,走向了彼此救赎,吴苔花也在儿子的帮助下,重拾自我。
正是吴苔花误入传销组织的这段“歧途”,阴差阳错地将真正的吴苔花唤醒出来,而这段歧途或许是任何一个边缘的、弱势的“娜拉”群体都要经历的精神困境的外化。正如电影《七月与安生》中七月与安生在青春期的躁动、狂欢与争吵,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中久困樊笼里的许红豆,她们过往的经历何尝不是另一种“传销式的歧途”,而正是因为走过了歧途,真正属于自己的归途才会逐渐显现。这种“歧途”何尝不是黎明前的那段深不见底的暗夜,何尝又不是另一种“奇途”呢?她们始终在谋求真我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尽管姿态并不好看,尽管头破血流,但始终饱含着对生命的激情,对生活的热望,以及对自我的期待,这是主体性迸发的高峰体验。










 亲爱的用户,“重庆”客户端现已正式改版升级为“新重庆”客户端。为不影响后续使用,请扫描上方二维码,及时下载新版本。更优质的内容,更便捷的体验,我们在“新重庆”等你!
亲爱的用户,“重庆”客户端现已正式改版升级为“新重庆”客户端。为不影响后续使用,请扫描上方二维码,及时下载新版本。更优质的内容,更便捷的体验,我们在“新重庆”等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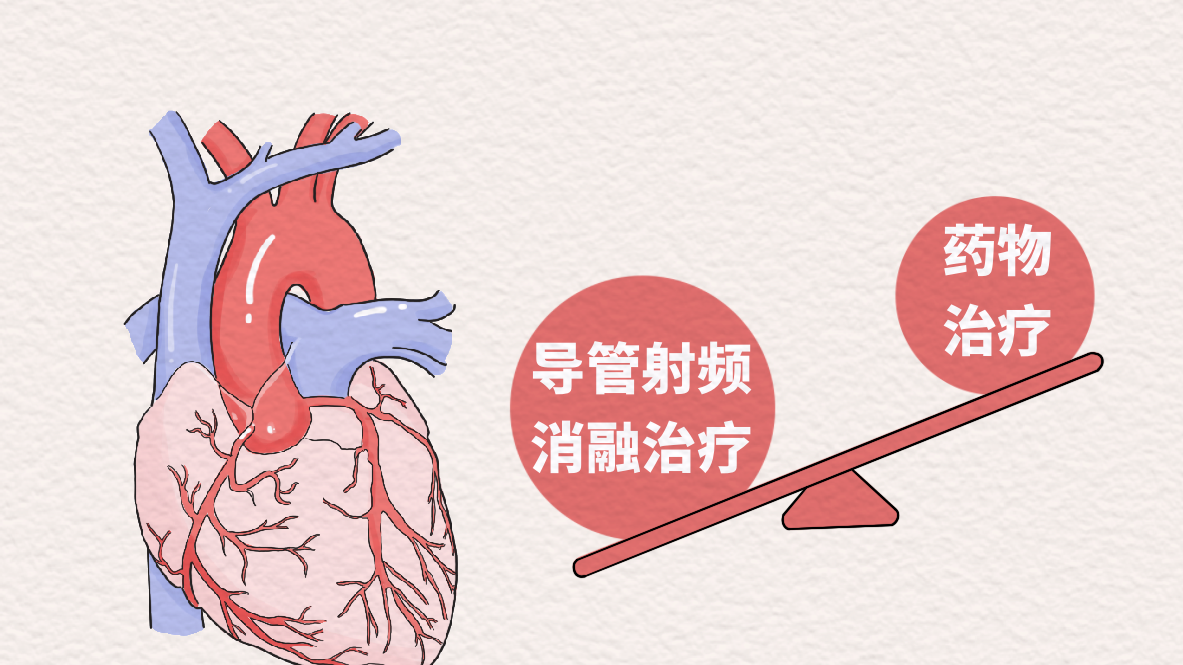

 数字报
数字报
 手机报
手机报 通讯员投稿
通讯员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