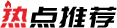学术的过程亦是生命的过程——读《我是谁?段义孚自传》
2024-05-04 17:59:09 来源: 华龙网 听新闻
作为现代地理学领域中赫赫有名的国际型专家,他最大的学术贡献在于开创了人文地理学这一崭新的研究方向。1976年6月,段义孚在世界权威期刊《美国地理联合会会刊》上发表论文《人文主义地理学》,在地理学界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奠定了段义孚地理学大师的地位。段义孚的著作,如《恋地情节》《空间与地方》《逃避主义》等,都是人文地理学领域不容忽视的开山之作与传世名篇。他被评为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2012年还获得了地理学界最高奖项——瓦特琳·路德国际地理学奖,其学术地位可见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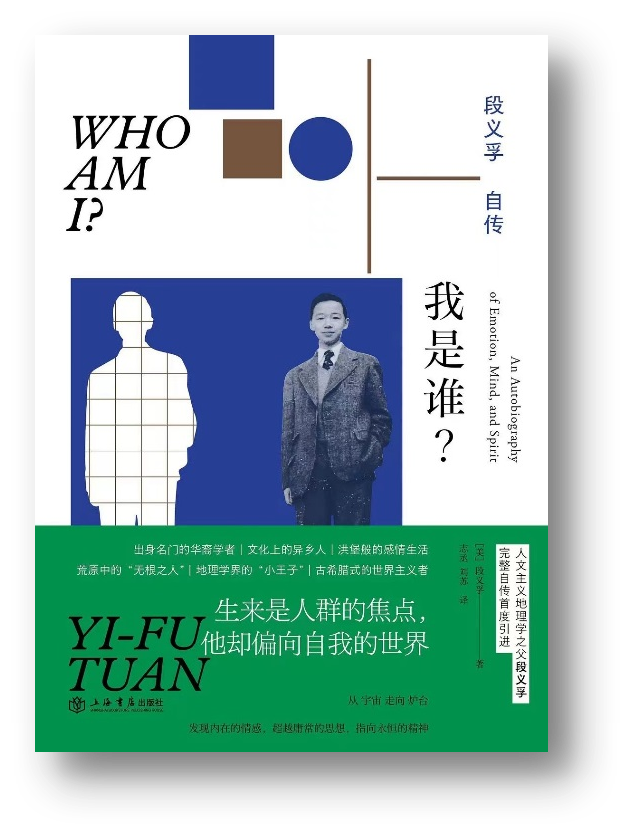
生命的反思:个人与时代的互嵌
段义孚出生于1930年的天津,于2022年去世。他的生命轨迹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密相连,恰好体验着世界格局的变动。这段人生与波澜起伏的人类历史彼此嵌套,塑造了他独树一帜的研究视角,进而也诞生出了这本与众不同的自传《我是谁?段义孚自传》(下文简称《我是谁?》)。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个人回忆录,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多种文化的交融,以及一个学者对世界深刻思考的结晶。
与编年体式的回忆录不同,《我是谁?》并未采用线性的时间线索来展开,而是用并列式的手法将本书分成六个部分:分别讲述了段义孚的个性、他对亲密关系的理解、对公共事件的理解等多个话题。以个人经历牵引出对公共领域的看法是本书的一大特色,这避免了人物自我作传时对个人的过分强调。阅读本书,读者可以明显感受到作者在撰写的过程,融入了自己与时代变迁紧密联系的深刻反思。
生命的彷徨:在漂泊中寻找依托
如书的标题一样,回答“我是谁?”成为段义孚主要的人生课题。这种对身份的追寻,与他个人的经历息息相关。他开宗明义地写道:“作为一个寻不到根的人,我天生就该自我审视。”何谓“寻不到根的人”?这在段义孚的人生中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这种无根在于地域空间上的迁移与游荡。如他所说:“我一直在不停地换住处,先是小时候与家人一起,长大后便独自一人。我的‘家’换了一个又一个城市——天津、南京、上海、昆明、重庆、堪培拉、悉尼、马尼拉、伦敦、牛津、巴黎、伯克利、布卢明顿、芝加哥、阿尔伯克基和多伦多。”
另一方面,这种“无根”还表现为情感上的无所依附。在描述父母双亲时,段义孚的文字充满了遗憾。父亲的严苛和自我,让童年时的段义孚又敬又怕。相比之下,段义孚与母亲的关系更为亲近,但面对家中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母爱总是很难面面俱到。因此,段义孚的童年总是努力争取母亲更多关注和偏爱,情感的无所附着在年少时就根植在段义孚的心中。成年后,终身未娶的段义孚没有找到令他长久深爱的人。这种身份的飘零感贯穿了段义孚的一生,为他后来选择地理学作为研究方向奠定了情感基础。
生命的方向:做一名地理学家
以学术为志业的人,往往将自己的生命经历纳入到学术研究中,此时学术的神圣性在于对个人意义的打捞,个体价值在学术过程中得到彰显。成名后的段义孚,常被问到的问题是:“你为什么是一名地理学家?或者,你为什么要称自己是地理学家?”对此,他回答:“我总是被一种不同寻常的恐惧所笼罩,那就是迷失方向。当然,没有人要迷失方向,但这种恐惧在我这里就有些过头了。我觉得,这给人带来的不适甚于身体上的病痛。当人迷失方向的时候,就是六神无主之时,你不晓得该如何选择脚下的路,哪条路会更好,就连前进还是后退都拿不定主意。生命缺失了方向感,便心无所向。所以,当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就认定自己要做一名地理学家,这样才不会迷失方向。”
同样的问题,北大教授戴锦华在接受记者提问时亦说道:“我这一生从开始时的不自觉,到后来高度自觉的状态是,我的学术必须与我的真实生命、我的社会生存与我的社会关注紧密相关。这种相关度以及我用个人生命去面对与体验它的真诚度,对我来说是首位的。”可见,对于这些顶级学者而言,学术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建构人生价值、承担历史使命的过程。如段义孚所言,“正是地理学才让我的目光始终朝向这个世界望去,并发现尽管有那么多惊骇可怖和虚空无益的事物,但这个世界总体上还是美好灿烂的”。
生命的升华:“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
进而言之,学术研究在引导我们认知自我价值之余,还拓宽了我们对生命的感受。在书中,段义孚区分了两种“成功”的感受:一种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比如一次成功的演讲后人们的满堂喝彩,再如《高等教育纪事报》对一位学者的溢美之词,又如滑铁卢大学校长亲授的荣誉学位。而另一种成功则是一种“能为生命给予最深满足感的平凡的经历”。这种“平凡”是指普通人可以平等地享受到的幸福。这种成功,来自于社会对生命本身的肯定,无需你成为别人,只需要坚定地做自己,就可以拥有如他人同样丰厚的幸福。这是段义孚期待和向往的成功,即所谓的“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这是学术研究与生命历程相结合后,生命境界的又一种升华。
文/董小玉 卢松岩
责任编辑:王景行









 发言请遵守新闻跟帖服务协议
发言请遵守新闻跟帖服务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