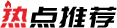巴渝文苑 | 与鼠斗 其乐无穷(散文)
2024-06-25 18:07:41 来源: 华龙网 听新闻
文/铁城
掐指算来,与鼠“断交”已有整三十年了。
那是1994年,我所在的单位盖了一幢职工集资楼,按职级、工龄和其他择房条件,我有资格挑选三至十楼的任意一套住房。
然而,为了彻底与深恶痛绝的鼠“断交”,我毅然选择了一套十五层以上的房屋。
起因是自记事以来,到分配此房之前的三十三年间,我曾与鼠打了无数次“交道”,并与之进行过反反复复的不懈斗争。
想起与鼠斗的前后经历,至今仍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真正与鼠“断交”后,我又深感释怀,不时向身边的朋友们调侃道:“与鼠相斗虽无共赢,但总觉其乐无穷!”
提起鼠,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鼠目寸光、贼眉鼠眼、胆小如鼠、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等关于鼠辈的众多词汇。
本文所述之鼠,确系在实际生活中相遇、相交过的真正的鼠。
在短暂的人生旅程中,我曾与乡村鼠、集镇鼠和都市鼠等三类不同地域的鼠打过“交道”。
青少年时期相遇的乡村鼠,因父老乡亲个个缺衣少食,鼠辈也跟着挨饿遭罪。乡村鼠个小体瘦、竖长、黄毛、胆小怕事,可头脑反应极快,动作灵敏迅疾。由于长期食不果腹,藏于洞中害怕见人。因此,乡村鼠才是人们常说的贼眉鼠眼、胆小如鼠的鼠。
与鼠真正意义上交恶,是在我五岁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
那天夜里,因白天贪玩疲累得一塌糊涂的我,上床就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正待我乐呵呵地,即将从玩伴手中接过最喜吃的麦粑时,一阵剧痛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惨烈的哭叫声,将忙着家务的父母、哥姐招到了床前。
母亲忙不迭地掀开蚊帐,就着昏暗的油灯一看,我满脸鲜血不说,眉宇间自上而下还有一条冒着鲜血的伤口。
闹了半天,大人们才明白:原来是在我枕边觅食的鼠,不知遭受啥惊吓后拔腿开跑时,锋利的鼠爪将我眉宇蹬出了一条近两厘米的伤口。
时至今日,当年被鼠蹬伤的地方,仍留有一道明显的痕印。
从此之后,我内心深处就十分痛恨贼眉鼠眼,啮食粮柜偷吃粮食的鼠。
懵懵懂懂的我,背着大人花钱买回钓鱼钩、线,试图将鼠钓到后在父母面前逞逞能!
怎么也没想到,我耗钱、耗时、耗精力的用心之举,却惨遭鼠辈的不管不顾和不理不睬。
后来才知道,鼠十分灵巧敏锐,一般情况下,它们不会轻易上“钩”!
相遇集镇鼠,是1981年下半年至1986年上半年。
为尽力搞好自筹自办的公社文化站,我主动向县文教局领导提出,将分居两地的妻子,从城里调到乡下的公社中学后,学校领导在房屋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腾出一间近四十平米的教室,作为我一家三口的住房。
说是教室,其实是一间寺庙厢房。
当年的龙河中学,曾是远近闻名的徐家寺。
此前的徐家寺,是当地人们逢年过节祈福祭祖、上香拜佛的一座历史悠久、古色古香的寺庙。徐家寺分上下殿和左右厢房,我的家是右厢房。旁边,还临时搭建起两间近百平方米的学生寝室,常年居住着四五十名住校生。
正因有那四五十名住校生,我所相遇的集镇鼠不为吃喝发愁,长得肥头耷耳,走起路来漫不经心,还像鸭子一样左右摇摆……
集镇鼠肥头耷耳、大模大样的派头,让人看上去很不是滋味。
肥硕白胖的集镇鼠惹我烦恼,源自鼠辈“狗改不了吃屎”的秉性。
鼠系啮齿类动物,哪怕它们一日三餐不缺吃喝,仍改不了啮食人类家具的秉性。据说,鼠一天不啮吃东西,它们的牙就会痒痒得难受至极。
盘踞于我家阴暗之处的鼠,不分白天黑夜,瞅准我和妻白天上班或深夜熟睡之机,肆无忌惮地啮食衣柜、床头柜以及我那心爱的三抽柜。
七八十年代的家具,基本上都是由床、衣柜、平柜、三抽柜和梳妆台、饭桌等六大件组成。条件较好的也配置有角柜、橱柜和洗脸架之类附属家具。
对于自小就喜欢读书的我来说,三抽柜当仁不让地成了心爱之物。
三抽柜长一米二,宽八十、高九十公分,由一大两小三个抽屉和一个柜子组成。
我家的三抽柜,既是书架和书柜,又是写字台。
那时的我,总是将一个简易书架靠墙摆放在三抽柜柜面,把常用书籍分一二三排陈列于书架。不常用需保存的书籍,就一股脑儿装进右下方的柜里。
十分恼怒的是,搬进学校那个家不足半年,三抽柜、衣柜和床头柜均被那群可恶至极的集镇鼠啮食得千疮百孔、惨不忍睹。
更让我气愤之极的是,当我打开书柜,搬出存放在柜中那些不常用的书刊时,竟发现多部书刊都被鼠啮食得七零八落、面目全非。
第二天,忍无可忍的我,便独自一人悄无声息地到供销社生产资料门市部,买回了十几包老鼠药,神不知鬼不觉地放置到鼠们经常出入的地方,喜滋滋地静候着鼠辈“全军覆没”的佳音。
一天一夜过去了。
两天两夜过去了。
三天三夜过去了。
信心百倍、满怀希望的我,除捡到一只幼鼠死尸外,压根就没看到鼠辈“全军覆没”的喜人局面。
夜深人静时,鼠依旧成群结队地啮食着家具。我却一声不吭地躺在床上,苦思冥想着怎样收拾它们!不时,也会将床头板拍打得震天响,将鼠们吓得屁滚尿流、魂飞魄散。
如此这般坚持了一段时间后,耿耿于怀的我,花五十元巨资在街上购回五个捕鼠神器“逮鼠夹”,不吭声不出气地悄悄将“逮鼠夹”摆放于鼠辈的必经之地,又一次高枕无忧地静候着佳音。
事实证明,“逮鼠夹”真是名不虚传。不到半天时间,就有两只大鼠中了招。
为泄愤,我将逮鼠夹夹住的两只大鼠取下后,用事先准备好的绳索绑牢,挂在家门前“示众”,以此震慑震慑其余鼠辈。
正兴致勃勃地憧憬着日后巨大捕鼠成果时,我们两夫妻便接到了调离公社中学的正式通知。
进城后,我又遭遇了见过世面、趾高气扬,皮囊发亮、油光水滑,人前人后从不贼眉鼠眼的都市鼠。
城里的新家是底楼,房前有口化粪池,房后有条餐厨下水道。其地理环境,很是适宜鼠辈生存和繁衍。
那些见过世面,胆大妄为的都市鼠根本不怕人。无论是白天和黑夜,它们都会成群结队,大摇大摆地进进出出。
一天中午,几个乡下来的朋友正在客厅品茶谈事。我下意识地看到四五只鼠在客房门口张望,试图横穿客厅通过主卧翻窗而出。
见此情景,我用力将脚在地上一跺,本想将鼠吓回客房钻入洞中。
哪曾想,听到跺脚声的鼠们,非但不掉头回客房,反而目中无人飞也似的“呼、呼呼”穿过客厅和主卧,翻越窗户跳到了房外。
被鼠情惊扰得有些目瞪口呆的乡下朋友,缓慢地回过神来苦笑着调侃说:“你们城里硬是不一样,连鼠都与众不同,胆识过人。”
最让我忍无可忍的是,鼠们鸠占鹊巢,胆大包天地在我新买回的三抽柜里繁衍生仔!搬进新房不久,我就发现城里的鼠,比乡村和集镇还要多。又悄悄买回鼠药和鼠夹,如此这般地“施计”和“布阵”,可从没收到过丁点儿效果。
毕竟,此次相遇的是一群见过世面的都市鼠。
一天深夜,我忽然听到少有人出入的客房里,传来了一阵阵“唧、唧唧”“唧、唧唧”的仔鼠声。
进客房认真查看后,才发现鼠窝就在书柜里,仔鼠的“唧、唧唧”声,也是从书柜里传出来的。
接下来,我就亲自策划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捕鼠之战。
一天晚饭后,我轻手轻脚、不声不响地摸黑躺在客房床上,睁大双眼屏住呼吸,恭候着鼠们到书柜聚会。
不足半个时辰,就有七八只肥硕光滑、皮囊发亮的鼠依次从早已啮食出的洞里钻进了书柜……
待鼠们狂妄至极地在我心爱的书柜里寻欢作乐时,我不声不响猛地一下翻身起床,迅疾用双手左右开弓,一只手用事先备好的旧衣服堵住洞口,一只手用编织袋自下而上套住柜门。然后慢慢地将柜门拉开一条缝,一手紧攥编织袋口,一手用力拍打写字台台面。随着“呯、呯呯”的敲打声,柜里乱成一团的鼠们,慌不择路地朝着编织袋鱼贯而入,悉数成为瓮中之鳖。
大获全胜的我,喜形于色地将装有八只巨鼠的编织袋放到小区空地上,引来近两百名邻居围观。
与我一墙之隔的邻居汪武,赶忙拿出自家的秤一称,八只鼠竟足有五公斤重,顿时将围观的人们,一个个惊得瞠目结舌。
三十年过去了,基本与鼠“断交”的我,不时回想起那些时日与鼠之斗的历历往事,仍有一种喜不自禁、其乐无穷的快感。静下心来仔细一想,人鼠之间为啥会长此相斗,永无宁日?其因恐怕就是鼠辈生性好吃懒做,不劳而获。除此之外,是因为乡村、集镇和都市,仍有鼠辈生存繁衍的洞穴和环境。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徐云卿









 发言请遵守新闻跟帖服务协议
发言请遵守新闻跟帖服务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