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渝文苑 | 下馆子(散文)
文/铁城
下馆子,也有人将其说成“煞馆”,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是人们当年最喜欢听的一句话。
十一二岁时,常听三姨爹和四姨爹对父亲说:“铁大哥,下场我在合兴请您下馆子”。
“铁大哥,说好了端午节后第一个赶场天,在葛兰街上米市堡等齐,我请你和陈幺哥下馆子”。
下馆子,是请客吃饭的意思。
在那普遍缺吃少穿的年代,有人请你下馆子,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幸事。
三姨爹和四姨爹与父亲不同,父亲是一个颗字不识,老实巴交的农民。三姨爹是新疆G丫拖拉机厂工人,解放初期为分土地才回老家,还有一手精巧的竹编手艺;四姨爹本就是武陵县川江厂端铁饭碗的工人。
每逢年节,三姨爹、四姨爹到我家做客,他俩都会穿得伸伸抖抖、像模像样。用母亲的话说:“看你三姨爹、四姨爹多有本事,人家找得来活钱,穿的是衣服是衣服,裤子是裤子。”说着说着,母亲还会一脸不屑地将父亲瞪上两眼。
看到这样的情形,我可不服气,总想为不多言不多语的父亲抱打不平。心想:父亲穿的衣裤虽是补了几个疤,还不是像他们那样衣服是衣服,裤子是裤子!别人总不会说他穿的是连衣裙吧?想是这么想,可我碍于情面,还是没把这话说出口。
由于职业和经济收入的差别,父亲他们三连襟下馆子,多数时间都是两个姨爹请父亲。当然,也与母亲在她五姊妹中排行老大的地位有关。
那时下馆子,几乎都是“老三篇”。一碗炒肉片,一碗猪心肺炖萝卜,一碗炒血旺或血旺汤,外加一碗“帽儿托”。
提起“帽儿托”,不得不格外哆嗦几句。
计划经济时期,无论买啥都得凭票,下馆子与在伙食团吃饭一样,也是买几两吃几两。
那时,每个食店的饭甑子前,都会站着一个姿色姣好的女服务员。
甑子的右边放个脸盆,脸盆里装着水和一个汤碗。甑子的左边,重叠摆放着数十个比汤碗稍大一些的饭碗。
那时下馆子的人,一般吃饭都在二三两之间,极个别特能吃的除外。因此,脸盆里水泡着那碗,满满当当就是二两米的饭。
每当食客将饭票递给服务员后,服务员就会笑眯笑眯、动作麻利地用右手拿起面盆里那汤碗,在甑子里刮满一碗米饭后,左手端起饭碗相互用力一扣,“帽儿托”就形成了。雪白的大米饭是“帽儿顶”,黑里巴几的饭碗边是“帽儿檐”,实在是太形象不过。
正是跟着父亲经常下馆子,才让我观察到一个秘密,以至长大后无论在哪上班,都会想尽千方百计与食堂里的师傅搞好关系,确保自己肚子不挨饿,每月还可节约几斤粮票。
经过反复观察我发现,服务员在为客人打饭时,遇到熟人就用力多刮几下,“帽儿托”也变得紧紧实实;若是陌生人,服务员会轻手轻脚地刮上几下,那“帽儿托”就明显地松松散散。“帽儿托”的一紧一松,食客呑进肚里的米饭,不用说就会有着天壤之别。
也是幼时经常跟随父亲下馆子,我把血旺也吃出了感情。
时至今日,但凡是我请客吃饭,只要条件允许,都会自然不自然地点上一份泡椒血旺或红烧血旺。
前不久,与堂弟治平在千里之外的西双版纳相遇,我也依旧点了一份红烧血旺,以至治平刚尝一口,便喜出望外地惊呼起来:“哥,这血旺是真猪血,看起满是风空眼,嚼起也还有些粘巴”!顿时,我和治平都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起来,惹得满堂食客的目光齐刷刷地射向了我们。
治平说那话,一语道破了几十年前“乡巴佬”下馆子,吃血旺辨识真假的天机,叫我咋不仰天大笑……。
作者简介:铁城,正名余德成,群文副研究馆员。
中国散文学会、华夏精短小说学会、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重庆市秘书学会副会长,曾任《办公室工作》杂志总编辑。
出版报告文学集《我和我的老乡们》、社科论文集《探索之痕》、长篇通讯文集《笔尖下的传奇》、散文诗歌集《故土留痕》和短篇小说集《那年那月那些事》等专著五部。有诗文发表于《重庆晨报》《西部散文选刊》《作家新视野》《贵州民族报》《重庆科技报》等。











 亲爱的用户,“重庆”客户端现已正式改版升级为“新重庆”客户端。为不影响后续使用,请扫描上方二维码,及时下载新版本。更优质的内容,更便捷的体验,我们在“新重庆”等你!
亲爱的用户,“重庆”客户端现已正式改版升级为“新重庆”客户端。为不影响后续使用,请扫描上方二维码,及时下载新版本。更优质的内容,更便捷的体验,我们在“新重庆”等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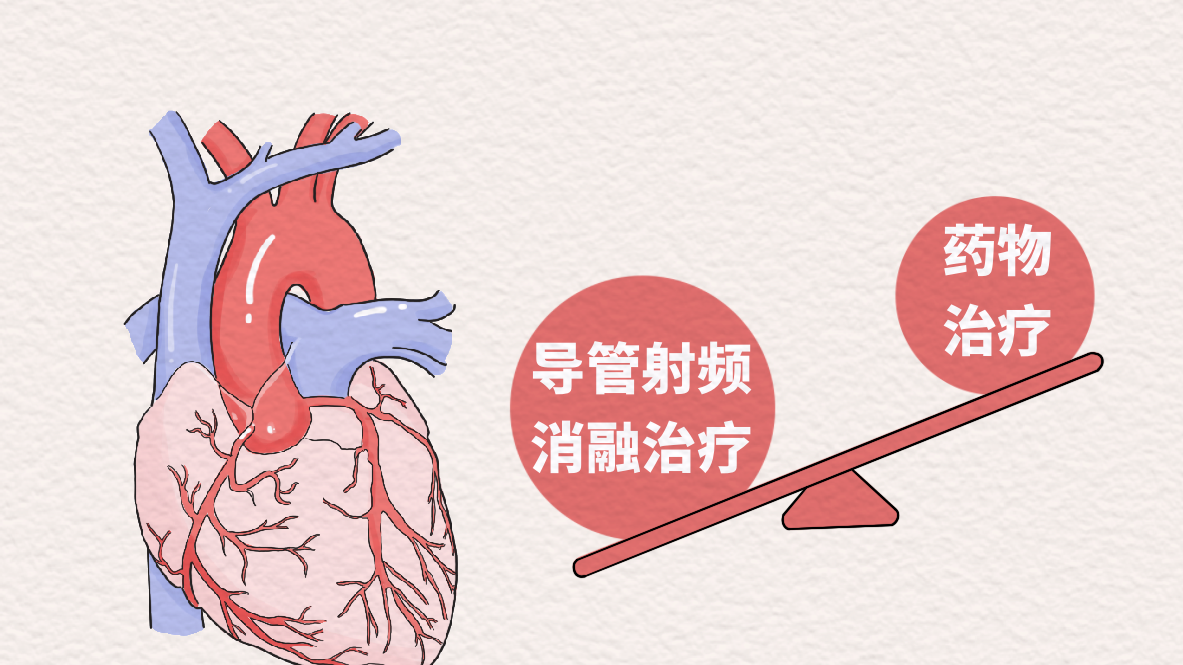

 数字报
数字报
 手机报
手机报 通讯员投稿
通讯员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