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渝文苑 | 过年
文/石楠
最难以忘怀的,还是在西北农村过的年。
西北农村的年,差不多是从腊月头开始,二月二龙抬头这一天结束,感觉整整要持续两个月。进了腊月,记忆中要下几场大雪,大雪的到来,提醒着辛苦一年的人们,年已经不远了。辛苦一年的人们在几场大雪之后,也就不约而同地放下农活,开始准备过年了。
准备过年的第一件事,便是杀年猪。记忆中,整个村庄从腊月初一一直延续到腊月二十四,除了腊月初七、十七,我至今也没搞明白这两天为什么不杀生。杀年猪的时候孩子们最开心的事儿,便是把猪的膀胱充气当足球踢。谁家杀年猪,都要给村庄里德高望重的老人端一碗香喷喷的杀猪菜,有猪油爆炒的土豆片、有肥肉炒粉条、猪血和面摊饼……我小时候跟着爷爷吃了很多家送来的杀猪菜。至今回忆起来,那是最好吃的杀猪菜,那是永远盛不满乡村亲情、温度的一个蓝边粗瓷大碗。虽然那是一些久远的记忆,但一切又那么刻骨铭心,一切那么深邃,一切那么鲜活……
在腊八那天,每家每户都熬腊八粥。西北农村的腊八粥很简单,主要是小米,光景好点的人家,放点大米、大枣、红糖。这种特制的粥,小米的黄色里透着大米的白、大枣的红、红糖的黑……可是细一想,这不是粥,它有它自身的骄傲,它倒是西北农业社会的一种顽强精神的表现,适应自然环境的体现。
腊月二十三日过小年,记忆中还保留着“送灶神”的习俗,这天晚上家家送灶神。天擦黑用香烛纸钱把灶神请到灶台上,家家户户统一吃的是扁豆面做的搅团,送“灶神上天”,希望来年有个好收成。现在,扁豆面价格也比小麦白面粉高上几倍。享用扁豆面的搅团,是记忆深处家乡的味道。到了正月初五,家家户户还是吃搅团,迎接灶神,因为这天灶神从天上“回来了”。
转眼间,到了除夕,除夕第一件事儿是祭祖。等到太阳落山头,老少爷们端着香马盘从路口将已故的祖先接进家,寓意着和大家一起过年。妇女们早早准备好贡品,随着鞭炮声,将各种各样的贡品有讲究地摆在贡桌上,然后是三拜九叩等一系列祭祀礼节。祭祀礼毕,就分别给长辈磕头送祝福。现在想来,除夕磕头送祝福与正月初一的拜年是两种不同的情感表达,岁末年初都是一年重要的时间节点,一个代表着过去,一个代表着未来。
接下来,便是贴春联、一大家人围在炕上吃年夜饭。这一夜,很晚才睡,大家都在守岁。
正月初一,拉开窗帘望去,一夜之间,外面已成了银装素裹的世界,又是一场大雪。是啊,过年了,过年了,甚至能看到被白茫茫大雪压着的大地,透露着丰收的喜悦,树枝上的麻雀抖动着春天的喜悦,也无赖地叽叽喳喳,这几天又要挨饿了。孩子们三五成群的去给长辈拜年,最开心的不是长辈们一毛、两毛的压岁钱,而是长辈们允许拿点小米、筛子、绳子等套麻雀的工具。
到了正月初七,一年一度的社火开始了,一直延续到正月二十左右。五颜六色的灯笼、震耳欲聋的鼓声、雪白色的舞狮……社火的头家(组织者)有很大话语权,他可以决定社火队伍谁舞狮子、谁打鼓、到哪儿演出、前进的速度……他是我小时候最崇拜的人。印象最深的是元宵节的社火,十多支社火队伍齐聚一堂,等表演全部结束,鸡打鸣了,天都亮了。现在想来,乡村社会的爱恨情仇都能在这场大型社交活动中得以解决。有约定两家的驴互相借力共同犁地的、有约定互换土地的、有约定说媒提亲的、还有约定借种子的……
夜晚举行社火结束了,白天的秦腔大戏开始了,曲目有《下河东》《三对面》《辕门斩子》……小时候不喜欢看戏,感觉一群大花脸咿咿呀呀老半天,听也听不懂。现在有时听上一段秦腔,也很提神,重要的是,它体现了黄土高原的浑厚,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过了二月二,春风早已把春联吹褪色,甚至吹飞,意味着年已过完。大人们开始忙碌新一年的农活,孩子们也去上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大部分农村人到城市过年。
过年,这几年感觉在繁忙的城市里,似乎缺乏点年味。最令自己怀念的,还是西北农村过的年,虽然那时候物质条件不怎么好,但过年可以杀年猪、穿新鞋新衣、看社火……











 亲爱的用户,“重庆”客户端现已正式改版升级为“新重庆”客户端。为不影响后续使用,请扫描上方二维码,及时下载新版本。更优质的内容,更便捷的体验,我们在“新重庆”等你!
亲爱的用户,“重庆”客户端现已正式改版升级为“新重庆”客户端。为不影响后续使用,请扫描上方二维码,及时下载新版本。更优质的内容,更便捷的体验,我们在“新重庆”等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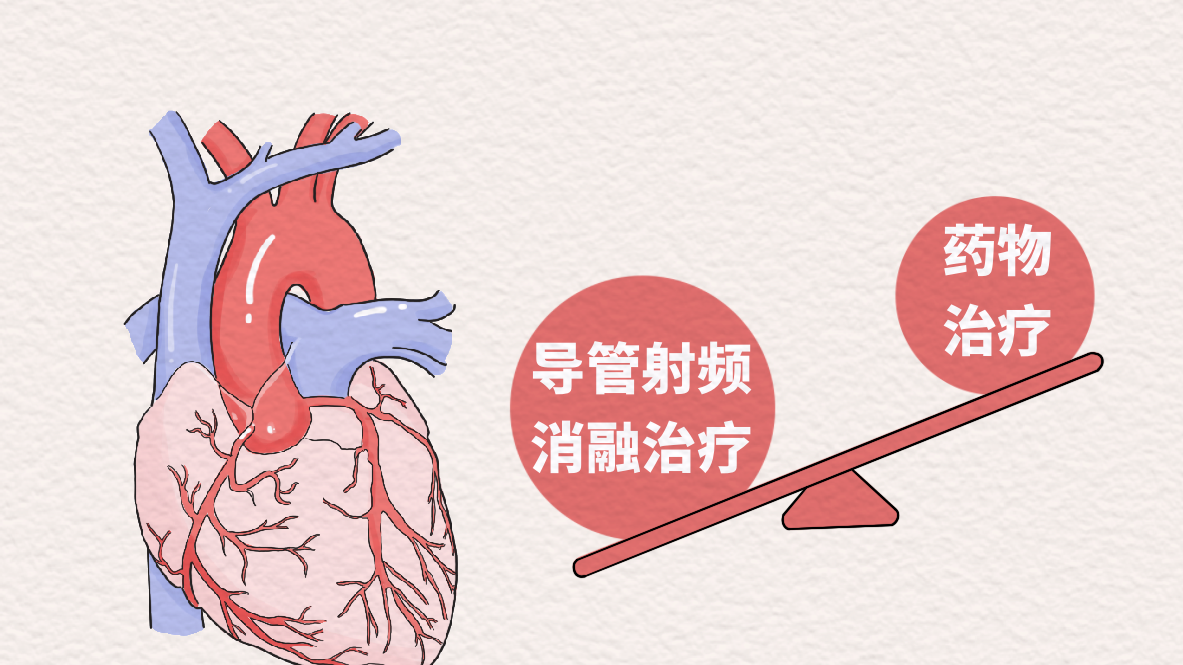

 数字报
数字报
 手机报
手机报 通讯员投稿
通讯员投稿



